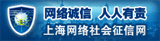100多年前,外國魔術進入中國,登上十里洋場的上海舞臺;
20世紀30年代,融貫中西,上海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魔術派別,一洗國際魔術界對中國魔術的歧視;
20世紀80年代,經過十年浩劫之后的“海派魔術”再登歷史舞臺;
2009年,“海派魔術”受到了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,閃耀光輝。
……
走進張小沖住在九亭鎮知雅匯小區的家,客廳里擺放著的中式古木座椅和歐式新古典主義的皮質沙發,把室內風格襯得頗有中西合璧的味道,一如“海派魔術”的元素風格。37歲的張小沖,是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“海派魔術”的唯一傳承人。民國時期,外祖父張慧沖開創的“海派魔術”叱咤上海灘,風靡東南亞,為中國魔術贏得了尊嚴和地位;從而,也鋪就了母親張慧慧和張小沖本人在“海派魔術”中的傳承與發展之路。
外祖“叫板”聶哥拉 贏得尊嚴驚國人
1930年7月,德國籍猶太人,國際著名魔術家聶哥拉來到上海,在夏令配克戲院(如今新華電影院)演出,廣告宣傳中充滿著對中國魔術界的歧視,并稱這一回他帶來的《腰斬美人》節目可稱雄于世界,倘若哪位中國人能窺透其中秘密,并照樣表演一遍,他愿輸1000美金云云。
節目中,一名女演員站在僅容一人之身的小立柜中;關門后,寬寬的兩把刀橫插進立柜,將柜體分成3段,然后柜體再被豎段剖開分向兩邊。首場結束后,愛國心極強的張慧沖決意出手挑戰,憑著已有的魔術經驗,很快地,他制作出了比聶哥拉更為精湛的可以兩面開門的《腰斬美人》,不但把“三分體”的上中下柜門全部打開,觀眾們還可以看到被分割開來的女演員的存在。
張慧沖與聶哥拉“叫板”讓國人驚詫,頓然成了當時上海灘的焦點。比賽結束后,“不怕貨比貨,只怕不識貨”、“為國增光國際勝賽魔術大家”等報道雪片般飛出,觀眾叫座,預售門票也是場場爭搶一空。
一炮而紅,這段傳奇是張慧沖魔術事業的起步。張慧沖,生于1898年,18歲進入吳淞商船學校求學,后來四處航海游歷世界。因為自幼對幻術表演充滿興趣,張慧沖在游歷時接觸了各種西洋魔術技法,積累了不少經驗。1922年,張慧沖入電影界,擔任過導演、編劇,是當時紅極一時的武俠演員,據說,影星阮玲玉便是在張慧沖的引薦下進入影壇的。先期的從影經歷讓張慧沖把戲劇表演融進了魔術。大型舞臺劇展示, “海派魔術”正是 的一大特色。一個流傳在吉卜賽的民間占卜術,被張慧沖搬上舞臺。觀眾只把想要解答的問題寫在信里,被炭火燒掉,張慧沖凝視著水晶球,就可以對問題做一一解答;一個占舞臺三分之一大的水缸里積滿了水,張慧沖穿著泳衣,帶著手銬腳鐐走進水缸,卻在一分鐘之后身著大禮服從觀眾席出現。這類節目迷倒了眾人。
拒絕照搬西方,張慧沖極力表現出中國文化。他時常穿著繡龍繡花的服裝上場,道具圖案里也富有民族特色,就連大幕也用帶蘇繡的孔雀花圖案,變換出的物品是中國式的宮燈、彩帶、萬花筒等。因骨子里的這番愛國主義情結,魯迅先生曾親切稱他為“慧沖兄”。
上世紀50年代,張慧沖的魔術事業達到了鼎盛,曾率自己的“巨型魔術團”在龍門劇場連演18個月,前后更換3期節目,每期巨型魔術達100多套,一次演完,創下了中國迄今為止巨型魔術最全、規模最大、連演時間最長、觀看人數最多的紀錄。此后,又應邀在中南海表演,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和肯定。
把玩道具成家常魔術熏陶他成長
十年浩劫一度切斷了“海派魔術”的發展,母親張慧慧無法繼承父業,下放到了江西省金溪縣雙塘公社,但自小就跟著外祖父到全國巡演的母親沒有因此放棄魔術,私下里仍然刻苦練習。在一次公社的會演上,張慧慧的表演終被金溪縣文工團看中,后又被推舉到撫州市文工團擔任魔術演員。
有一位做魔術師的母親和一位做道具師的父親,張小沖在魔術的環境出生、長大。20世紀80年代初,魔術重現舞臺,那時,張小沖5歲。母親開始四處巡演,走到哪里就把他帶到哪里,于是,后臺成了他小時候待的時間最長的地方。
“母親大多在晚上演出,上臺后沒人管我,就把我往幕后一放。張小沖回憶道。有一次,母親在臺上表演,張小沖自顧自地就走上去了,站在旁邊看。因為不能“出戲”,母親沒法理會他。直到工作人員發現,趕緊把張小沖抱了下去。當時,“ 臺下哄堂大笑,我對那笑聲的印象特深。”熟悉追光燈和幕布拉開的感覺,熟悉從后臺的視線看現場,舞臺漸漸成了張小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“那個年代,道具很珍貴,每一樣都要自己做,有錢也買不到成品。所以,母親的道具箱從不讓我碰。”越不讓碰,就越好奇魔術箱成了張小沖兒時最感興趣的玩具。一趁母親不注意,張小沖就拿來擺弄。小小機關能讓一朵黃花變紅花,還有神奇的假手指,各種套環,稀奇古怪的道具吊著張小沖的胃口。有一回,他一不小心碰到按鈕,各種花瓣爆了一地,張小沖卻怎么也不會還原,巴巴地迎來了母親的一頓訓斥。“很多秘密都暗藏在里面,大多數情況下看也看不懂。”
在拜訪魔術專家時,母親會特意帶著他,小學時,母親讓他“升級”做了自己的助演。從最簡單的動作做起,抬頭挺胸走臺步,傳遞物品,展示給觀眾……每個動作都要求精細到位。剪手帕是他的第一個助演魔術。把剪刀尖對準自己的手心,把刀把朝向母親,再做一個干凈利落的示意。“外祖父要求很高,母親對我的要求也高。”后來,表演經歷多了,每到兒童節,張小沖的魔術成了必演節目。
融入了戲劇元素“海派魔術”得創新
當年,外祖父因“人體三分”一炮而紅,張小沖帶著改進了的“人體五分”在上海世博會魔術專場上展示風采。
“母親從沒要求我長大了一定要做魔術師,但這種選擇好像是自然而然的。”1996年,決意將“海派魔術”傳承下去,張小沖在高考時填報了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。“藝考都是圍繞著‘聲臺形表’去做,但考試時我演的是魔術,大概給考官留下的印象還不錯,入學后班主任找到我,問的第一句話是,你會變魔術吧?”
那時,上戲沒有魔術專業,張小沖常常自己鉆研。如何把戲劇元素融入魔術表演中去,年的科班表演讓張小沖開始了對4 “海派魔術”的學術性思考,同時,也體會到外祖父作為電影人對魔術的理解。“很多魔術表演是刻意的,當你在演的時候,觀眾能感覺你在‘變’魔術。但我希望把魔術內化成自己的一部分,讓魔術與魔術師成為一個整體,讓人感覺不到你在‘演’,而是真實的。”
大型情景魔術《紅》,是他在探索戲劇與魔術融合的第一部作品,也是他比較滿意的作品之一。2003年,張小沖因為這個節目,拿到了國際魔術比賽的新人獎。《紅》講述的是一段20世紀30年代舊上海的愛情糾葛。在一間夕陽西照的小屋里,男主人公憂傷地找尋著曾經像火一般熱烈的感情。在“第三時空”里兩人的影子癡纏交織,慢慢消失又漸漸出現。然而,回到現實世界,兩人卻始終無法觸摸彼此。最后,女主人公化為蝴蝶飛走留給男主人公的只有一條紅色圍巾。
張小沖用了外祖父魔術中的“影遁”手法,加上歐洲電影的“鏡頭內部蒙太奇”效果。這部魔術,花了張小沖兩年的時間,故事的靈感來源于張愛玲的小說。張小沖是認真的,設計、布景、燈光、舞美都要親自操刀。細致到演員頭上戴的發飾,頂針上的一支小蝴蝶結都要親自設計。
這部作品也是張小沖與妻子嚴格意義上的首次合作。
緣起于“空中魔術”愛情給創作靈感
愛情,既關乎魔術,也關乎生活。在張小沖的每場表演里,都有一位穿著紅色長裙的女子。翁驪娜,東方航空公司的空姐,是張小沖的助演,也是他的妻子。
剛讀大一時,從香港參加完魔術比賽,張小沖戴在脖子上的胸牌還沒來得及摘下來,就急匆匆上了飛機,正值當班的空姐是翁驪娜。翁驪娜看見胸牌后興奮地問:“你會變魔術嗎?”張小沖回答:“當然。”“能表演一個嗎?”于是,張小沖拿出一枚硬幣,假裝咬掉一半吞下去,之后,在翁驪娜的耳朵旁神秘地畫了個圈,硬幣還原了。翁驪娜更好奇了,一路追問“這是怎么回事呀?”
那次聊天后,兩人互留了電話號碼,也開始了長達10年的馬拉松戀愛。因為翁驪娜有舞蹈功底,很爽快地答應了在業余時間為張小沖做助演。如當年外祖父航海時勤于搜集魔術資料一樣,每到一處,小翁總記得為張小沖買回當地的魔術雜志和書籍。
愛情給了張小沖許多靈感。名為《雪》和《雪之魅影》的散文化情景魔術,就源自于這次飛機之旅的愛情。如今,兒子乖乖已經兩歲了。在乖乖眼里,魔術就是生活。張小沖喜歡在兒子面前把瓶子里的東西變沒,又變出一個新玩具。于是,每一次看到瓶子空了,乖乖總是嚷著讓變出一樣新東西。爸爸的瓶子是個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萬能寶貝。談到家族傳承,張小沖說,對于兒子,他沒有任何要求,只要兒子喜歡。
公開揭秘不忌諱 推動魔術大發展
外祖父張慧沖留給后世的不單是數百個魔術節目。1953年,張慧沖將其所創的主要節目匯集成了《魔術》(上、下冊)一書公開出版發行。把鉆研的新概念和新技術告訴大家,讓更多的人了解魔術、熱愛魔術,張慧沖開創“海派魔術”的最終目的就是如此。
去年11月,張小沖的《海派魔術》一書出版了,把外祖父生前的代表作與自己近些年所創作品的秘密梳理公布于眾,這種讓不少魔術界人士最忌諱的事,卻成了他堅持要做的事。張小沖說:“不必保密,外祖父生前曾在報紙上發表《我愿意這樣做》的文章,因為只有相互交流,不斷改進、創新,才能讓魔術發揚光大。”要做一個不斷創新的魔術人,張小沖說這是他作為傳承人的一份責任。“目前,我還沒想過要讓‘海派魔術’達到何種程度,但這一定是不斷追求創新的過程。”如今,張小沖除了專場魔術表演外,還在小學、中學為感興趣的同學們講授入門式課程,也常出入于上海大學、上海師范大學等高校做魔術表演講座,參與各種學術研討,走進社區為居民們表演節目。“一直堅持下去,這就是對‘海派魔術’最好的發揚和傳承。”張小沖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