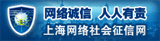位于浦東的張江高科[9.39 2.29%]技園區,是立志要成為金融中心的上海現有為數不多的制造業基地之一。盡管漲薪、人民幣升值等等對園區里為數眾多的高新技術企業影響還不算很大,但敏感的人還是注意到,那場源自珠三角的加工制造業“生存風暴”,正在日益逼近。
分布于上海市郊其他區域的不少民營鋼鐵、機械企業,沒有那么幸運,它們中的一部分因難以應對成本上漲、經營虧損的壓力,早就開始撤離上海,遷往安徽、江蘇和山東等地。
加薪不加班
今年30歲的趙勇,是張江高科技園區內一家代工企業的員工。盡管這家企業名氣和規模遠不如富士康大,但業務模式與富士康有諸多相似之處:沒有自己的品牌,產品90%以上都出口到日本、韓國和歐美各國,員工人數眾多,很大一部分是一線操作工。
在這家企業干了7年的趙勇發現,今年以來廠方變得格外“摳門”了:金是該廠生產耗用的主要原材料之一,現在不但其正常用量要嚴格管控,連廢品也不放過,比如工業廢水中的金要設法回收,報廢的產品必須按是否含金分類,而不像以往一樣稱完重量一賣了之。原因是國際市場上工業用金價一直在漲,從年初至今漲幅已超過20%。
除了昂貴的金子外,在生產成本中只占很小比例的配套用料消耗也受到限制,連日常使用的產品包裝袋,以往一直是某國際知名品牌供應商的,最近悄悄換成中國本土一個不知名的牌子,價錢據說比原來節省了三分之一。
唯一不同的是,公司突然很大方地給一線工人每月增發了100多元的薪水。原來從今年4月起,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從每月960元,提高到每月1120元,上漲了160元。
趙勇說,占企業員工絕大多數的一線操作工,都是領基本工資加上加班費和獎金,這次大面積增加基本工資后,內部薪酬制度也隨即調整,工人獎金普遍下降,抵消了一部分漲薪的壓力。前不久端午節假期就只安排了少數生產線上的工人加班,管理崗位工資較高的員工都不允許加班,因為按規定廠方要發3倍的加班工資。
《勞動合同法》成“緊箍咒”
趙勇所在的這家企業,身處高科技園區,尚能享受一定的優惠政策,在上海從事傳統制造業的眾多民營企業,日子要艱難得多了。
溫州市龍灣區總商會上海分會副會長季學文告訴《中國經營報》記者,傳統制造企業如今在上海“已活不下去了”。
浙商與上海曾有一段蜜月期。從1999年到本輪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,一些在地方上羽翼漸豐的浙商陸續將總部遷往上海,希望借助這個全國甚至國際性的平臺,大展拳腳。
這些浙商大多從事傳統制造業。以溫州龍灣區企業為例,閥門、鋼鐵、機械和標準件是他們的強項,在上海外環以外的嘉定、松江、金山、青浦等區縣,到處都是他們的廠房。
季學文說,當時大家都覺得上海好,但后來現實的困境讓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得不選擇逃離。
一位號稱“閥門大王”的龍灣區老板告訴記者,因為原材料價格飛漲,現在他們只能得到極低的利潤,很多同行索性關掉上海的工廠,跑到全國各地尋找新機會。
這位“閥門大王”說,以前溫州地少人多,企業做大之后缺少發展空間決意離開,如今有些人又從上海回到溫州去了,因為家鄉政府給的政策更好,相形之下,上海不再是理想的投資地。
季學文認為,新頒布的《勞動合同法》讓傳統制造業廠商舉步維艱,上海對《勞動合同法》執行最為嚴格,最低工資標準為全國最高,而上海工人除了對工資水平期望值較高外,維權意識也極強。
季透露說,最近走訪過的一家企業,剛剛舉辦了一次業務水平考試,很多員工的專業技術知識平平甚至不及格,有關《勞動合同法》的答卷能得80多分,另一家企業的員工則因為加班費爭議調解不成,把企業告到了勞動部門。
據季學文兼職的浙商研究會近期了解,在上海的民營制造企業,大約只有三分之一能維持微利運轉的狀態,三分之一徘徊在保本邊緣,剩下的三分之一實際上是虧損的。
查看更多相關信息,可登陸松江第一招聘網>>